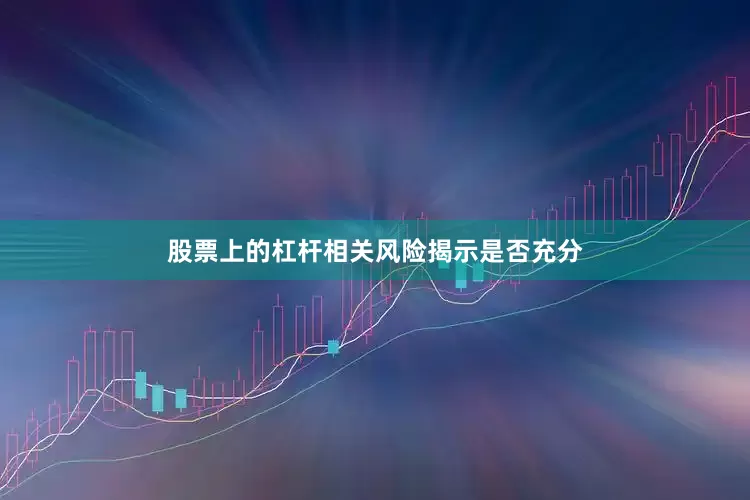小编暖心提醒,音乐相伴更有感觉~
樊靖
我家的“树根”断了
周末的清晨,天刚蒙蒙亮,手机铃声尖锐地刺破寂静。屏幕上跳动着母亲的名字,我的心猛地一沉——母亲从不会这么早来电,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我。
“儿子,你爸叫不醒,嘴巴还有血,快点来……”母亲的声音支离破碎,带着绝望的哭腔,“他昨晚洗澡摔了,但说没事,就自己睡了……”
“外伤导致脑出血!”外科医生的直觉瞬间让我给出了最残酷的判断。我赶紧拨打\"120\",并迅速往父母家赶去。
抢救的过程漫长得如同永劫,我脑海里全是父亲的样子:爱笑、贪嘴、喜欢在阳台晒太阳。我后悔自己平时把时间都留给了工作和自己的小家,陪父母的时间太少。
抢救结束,我悬着的心不敢放下,忐忑地走进医生办公室,看到了CT片上那片刺眼的出血灶——脑!我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
“脑干受压,双侧瞳孔散大,出血时间太久出现脑疝了。”医生声音低沉。
“真的没办法了吗?”虽然我自己也知道答案,但还是像以前患者家属追问我一样,恳切地询问医生。
“可以尝试开颅减压,但凭经验,预后极差,很大概率是植物人状态。”认真回答完我的问题,医生关切地问:“老爷子平时身体怎样?有什么心愿?”
“他有尿毒症,每周透析三次,腿脚无力才摔倒……”我艰难地说。
“出血量大,时间长。他血管脆,长期抗凝,手术止血难。术中减压,血压可能瞬间垮掉。”虽然知道我也是同行,但父亲的主管医生还是尽量用通俗的方式解释给我听:“就像一棵树,根断了,我们勉强扶住树干,但很难长出新芽了。”
急诊室门口,母亲掩面哭泣,亲人们围拢,悲声四起。“先气管插管维持可以吗?”我难以抉择。
医生理解地点头:“我建议先放个引流管,试着减轻点压力,再转ICU。我们可以尽量争取更多时间,给亲属在心理上有个缓冲。”
爸,别怕,我们终会再见
ICU里,父亲在呼吸机的辅助下安静躺着,仿佛沉睡。我握着他曾教我写字、陪我下棋的手,此刻,它温暖、柔软,却无力。
亲友陆续赶来,儿子也请了假,学着父母的样子为爷爷擦拭身体、刮胡子、剪指甲,泪水不住滑落。
当最后一位探望的亲属离开,我知道是时候了。“我们决定签字拔管。请帮帮我,让他没有痛苦。”我对医生说,签字的笔重逾千斤。
医生没有机械执行程序:“我们会用镇静止痛药。一会儿帮你一起给老爷子擦洗更衣。有什么需要,尽管说。”
我曾许多次对患者家属说出类似的话。但这一刻,寥寥几句,却温暖了绝望无助的我。
我一手紧握父亲的手,一手抚摸他的额头,感受那熟悉的温度一点点流逝。医生、护士们静静站在床尾,没有催促。护士递来热毛巾:“给老爷子擦擦脸吧,想说什么,告诉他。”
我俯身,在父亲耳边低语:“爸,你到站了,别怕。你先下车,我们终会再见。我会照顾好妈妈,照顾好大家。安心。”他的眉头,似乎舒展了一丝。
父亲走了。
医生和护士们细致地缝合切口,轻柔地翻转父亲的身体,用棉垫和酒精仔细擦拭每一寸肌肤,为他穿戴整齐。
这份守护尊严的温暖,给了我慰藉,也抚平了我内心些许的自责。
近几年来,我尝试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科普医学知识。父亲住院期间,我在自媒体账号发布了一张照片:病床上,我的手与父亲的手紧紧相握。这次,我的文字里没有科普,只有倾诉,文字下方的评论区里涌动着真诚的安慰与哀伤的共情。曾经,我努力医治患者、向网友传播知识;如今,患者和网友们也反过来自发地给予我鼓励和安慰。这些无声的拥抱围拢成一种新的力量——它不能起死回生,却支撑生者前行。

文:柳州市人民医院 樊靖
编辑:张昊华 杨真宇
校对:马杨
审核:秦明睿 徐秉楠
顺阳网-顺阳网官网-我国合法的配资平台-在线炒股配资服务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实盘股票交易配资早已改为17:00了
- 下一篇:没有了